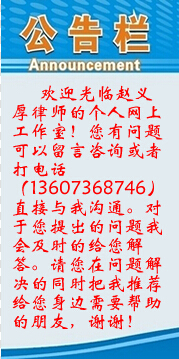【摘要】不少国家对住房租赁合同进行一定的社会控制,主要有宽严两种模式:租金管制和解约限制。从社会经济效果看,租金管制有助于保障住宅权,也有助于避免贫富分区和促进社会和谐,但会干扰市场规律,因而成本较高。以解约限制为中心的控制则不会过度偏离市场,同时可有效减少租赁合同中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中国目前城市自有住房比例较高,住房市场的主要矛盾是现有住房不足以满足城市化需求,因此不宜进行严格的租金管制,但修订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合同法,限制出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权利,同时规定租金调整参酌市场水平进行,将有助于维护住房租赁合同的稳定,减少出租、承租双方的策略性行为,降低围绕续约的讨价还价成本,增进社会福利。
【关键词】租金管制;租赁合同的解除限制;长期合同;住宅权
【正文】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租金管制会损害效率。[1]与此相一致,中国虽然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规定“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第54条),但实践中主要采合同自由原则,除规定租期不得超过20年外,允许当事人任意决定合同的内容(合同法第13章)。这一立场,在当前住房日益成为国计民生中重大问题的情况下,殊值探讨。
文章在结构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分析美国与德国的租赁控制法律制度,第二部分讨论租赁控制的社会经济影响,第三部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有关租赁合同规范的解释与完善提出思考与建议,第四部分为总结。
一、住房租赁控制的制度比较
目前世界各国的住房租赁控制大体可划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以租金管制为中心,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对租金、房屋维护、租赁期限等事项进行严格限制;另一种以解约限制为中心,着眼于维护住房租赁合同的稳定性,在此之外,不干涉租金数额。前者以美国纽约市为典型,后者以德国为代表。
(一)以租金管制为中心的租赁控制
在美国,租金管制并不是普遍现象,纽约市是个例外。根据1990年代的一项统计,纽约市占有全美被控制租赁住房的39%.[2]其最主要的租金管制规范是1969年的租金稳定法(rent stabilization law)和1974年的承租人紧急保护法(emergency tenant protection act),后来整合为租金稳定法典(rent stabilization code, rsc)。此外,纽约市的租金管制也受纽约州相关规则的调整。上述规则都汇编nycrr(new york codes, rules and regulations)第9编第2050条至2531条中。
1.租金数额管制。纽约大部分受租金管制的房屋都有一个由房屋与社区维护局(division of housing and community renewal, dhcr)确定的最高租金,其数额受建造与出租年代、房屋不动产税额、运营和管理费用、建筑结构与年限、建筑内出租房屋的数量等多项因素的影响(9 nycrr §§ 2201.3-4)。
对于大部分受租金管制的房屋,租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1-2年,出租人可向dhcr申请提高其租金,后者将参照纽约市租金指导委员会(rent guidelines board, rgb)的报告决定是否准许。9 nycrr § 2102.2-3列明了以下提高租金的规则:(1)出租人必须履行基本的服务,保证房屋处于安全、适居的状态。(2)一年内租金上涨幅度不得超过原租金的15%.(3)在房东对房屋的主要设施、建筑的主要部分进行了重大修缮后,可通过协议的方式提高租金,经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4)最终决定租金调整的机构是dhcr,调整后若有重大情事变化,可随时撤销或修正。另外,租金管制也不是永久性的。在满足条件时(如月最高租金经逐年提高超过了2000美元,并且通过税收证明表明,承租人每年的家庭收入总和超过17万5千美元),房屋所有人可以请求解除租金管制。
2.限制收回房屋。在纽约市,原则上只要承租人仍继续缴纳租金,出租人就不得收回房屋或驱逐承租人(9 nycrr § 2524)。欲收回房屋,出租人必须先通知承租人,遵循特定程序,满足严格的标准,包括:自用;非营利机构收回其出租房屋;承租人居住于他处,有关房屋不是承租人的主要住所;承租人严重违约或违法等。其他理由如拆除、大修、退出租赁市场等,还需要dhcr特别批准,由其授予“清房证明”(eviction certificate)方可实施。
3.防止规避。防规避规则是租金管制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披露与检查。纽约市有严格的出租房屋登记制度。要求房屋所有人在租赁关系确定后到dhcr登记包括所有人姓名、地址、出租房屋数量、登记日所收的租金数额、有关服务等信息(rsc § 2528)。如未及时登记,则只能按法定标准收取租金(n.y.c. admin. code § 26-517)。根据9 nycrr §§ 2103.8-9的规定,出租人还应全面保存关于房屋、承租人、租金、租期的信息资料以备管理当局检查。(2)维护与修理。降低维修标准,减少维修支出是出租人规避租金管制的重要手段。对此,纽约市的应对思路是:其一,通过立法确定房屋适居性标准,承租人可以根据该标准要求出租人提供必要的维修,若出租人无理拒绝,承租人可向相关的管理部门申请垫支维修。维修后管理部门可行使追偿权,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接管房屋,提请追究出租人的刑事责任。[3]其二,承租人可以因出租人的维修服务不合格而要求降低租金乃至免除租金缴纳义务(rsc § 2523.4)。其三,若不履行维修职责,出租人将被禁止申请上调租金(n.y.c. admin. code § 26-514)。从实际调查上看,纽约市出租房屋的状况非常好。[4](3)超标租金返还。根据有关规定,超出控制租金水平的租金支付无效,承租人可事后随时请求返还(9 nycrr §§ 2105.1-2)。根据1969年的租金稳定法,承租人甚至还可以向出租人请求三倍于超出部分的惩罚性赔偿(rsc § 2525.1)。(4)禁止转租牟利。按照纽约市的规定,出租人不得禁止承租人转租,以便承租人在短期离开所租住房后(如求学)仍可返回原租赁房屋居住。法律的限制只是:承租人转租的租金水平不得超过控制租金的110%,否则,次承租人可要求三倍于超过部分的赔偿(9 nycrr § 2525.6)。
4.租金管制的宪法争议。租金管制要得到贯彻,除了有立法机关的立法外,还要过宪法诉讼这一关。在1919年一个挑战华盛顿租金管制法的案件中,霍姆斯大法官认为住房租赁关涉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对它进行适当规制是正当的,鉴于战后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特殊状况,并且该法案的管制期限只有2年,因此不构成对私人财产权本质性的侵犯。[5]到1924年,霍姆斯在另外一个类似案件中认为战争状态已终结,因此租金管制不再合宪。[6]在此后的一系列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承继了霍姆斯的意见,一直重申租金管制需要有特殊的社会状况为基础。
认为租金管制应限于紧急状态的观点后来也有所松动,在第二巡回法院1969年审理的一个案件中,hays friendly法官甚至明确提出租赁管制立法没必要再以紧急状态或类似情况为前提。[7]此后很多州法院也作出了类似裁决。[8]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多数立法者还是选择了更稳妥的制度安排,如纽约市一方面将租金管制与出租房屋的空置率[9](vacancy rate)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还规定租金管制规则只在一段时间内生效,期限届满后,立法机关将对是否仍有紧急状态[10]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延展。[11]房屋所有权人挑战该制度的另一个思路是认为租金管制构成规范性征收(regulatory taking)或等同于征收,因而应遵循正当程序并给以充分补偿。这类案例[12]很多,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最高法院支持的先例。
(二)以解约限制为核心的租赁控制
相比纽约州直接管制租金的做法,德国和美国其他一些州(如新泽西[13])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立场,不直接干涉租金的设定,而是通过对租赁合同的解除施加限制来达到租赁控制的效果。新泽西州对租金的直接管控不多,但对住房租约的解除做了限制。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出租人仅在有正当理由(good cause)时才能解除租约:(a)逾期未缴纳租金;(b)破坏同住者或其他承租人的生活安宁;(c)损坏租赁住房;(d)严重违反物业管理规则;(e)在出租人合理提高租金后,承租人拒绝接受并拒绝履行缴纳租金的义务;(f)有关房屋状况违反了相关的健康或安全保护法律,只有通过整修或拆除才能改变此种违法状态;(g)出租人意图改变房屋的用途,不再用于居住目的;(h)出租人在合同期满后合理地改变租约内容,承租人加以拒绝;(i)承租人有某些针对出租人或其家人的民事或刑事违法行为;(j)承租人意图将有关房屋收回自用或将其出卖。[14]除新泽西州外,哥伦比亚特区、新南威尔士、康涅狄格等州也有类似规定。[15]当然,上述规则客观上也会发生限制租金的效果,但此种限制是在租约解除要件的大框架下实施的——出租人可以合理地调高租金,若承租人无理拒绝,则出租人可以解约。当然,对于何为合理,各州(如新泽西)并不像纽约市那样规定了具体明确的租金标准,只是强调不得“过度”(unconscionable)。[16]
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除“买卖不破租赁”[17]的规则外,对住房租赁合同并无基于社会化考虑的特殊规定。[18]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大量住房被毁而发生住房短缺,为了避免少数人借机提高租金发不义之财,德国开始通过单行法对租赁合同进行管制。[19]最初的管制相当严格,甚至强制剥夺房屋所有人的自由处置权,统一由国家分配和管理。此后随着经济转好,才逐渐有所放宽,[20]直至取消对租金的直接管制。[21]当前对住房租赁的控制主要体现为解约限制(kündigungsschutz)。[22]
德国的租赁合同制度主要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535条以下,其中第535条到548条规定了租赁合同的一般规范,适用于所有租赁关系;第549-577条专门规范住房租赁制度。
1.限制为租赁合同设置期限。在德国,欲签订定期的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必须在缔约时书面告知承租人限制租赁期限的理由。德国民法典主要认可以下三项理由(第575条第1款第1句):租期届满后,将房屋自用、供亲属或同住者使用;用合法的方式将房屋拆除、大修或置于某种不解除租赁合同会严重影响其进展的状态;准备将房屋租给服务提供人[23]居住。在租赁合同到期前,承租人可询问有关理由是否仍存在,出租人要再次以书面形式作出说明(§ 575 ii bgb)。该说明必须充分具体,以便承租人事后核实。[24]若出租人未履行上述告知或通知义务,或其限制租期的理由有违法律的规定,或有关理由不复存在,则承租人仍可主张有关租赁合同为不定期合同,在期限届满后继续使用有关房屋(§ 575 iii bgb)。
2.限制不定期住房租赁合同的解除。作为肯定要件,规定出租人只能在有“正当利益”(ein berechtigtes interesse)的情形下才能解除合同(§ 573 i s. 1 bgb),包括:承租人过失重大违约;出租人欲将房屋自用[25]及供亲属或同住者使用;出租关系的存续影响有关房屋的价值发挥,但房屋可以以更高的价格租于他人或出售除外(§ 573 ii bgb)。作为否定要件,规定出租人不得以提高租金为目的解除合同(§ 575 i s. 2 bgb)。
3.限制合同解除的社会化条款。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护承租人,德国法还设定了“兜底”性的“社会化条款”(sozialklausel):若承租人对租赁合同的利益大于出租人,解除对承租人、承租人家庭、承租人其他亲属而言过于严苛,即便出租人有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承租人仍可拒绝(§ 574 i bgb),例如承租人虽经合理努力仍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住宅(§ 574 ii bgb)。
4.限制租金数额与租金上涨幅度。在新租赁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原则上可自由确定租金数额。当然,和其他交易一样,租金数额也要受民法一般规则的调整,过高的租金将构成暴利而被认定为无效(§ 138 bgb)。另外,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若租金水平高于当地一般水平的50%,还可能构成暴利罪(§ 291 i stgb)。[26]德国法上对租金的限制主要着眼于租金上涨。当事人在订立租赁合同时,若对租金的调整有约定,则适用该约定,[27]若没有约定(通常如此),则只能根据住房所在地的可比租金[28]水平(ortsübliche vergleichsmiete)调整租金。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对上涨幅度的限制,根据第558条第3款,租金上涨的幅度在三年内不得高于20%.即使在最初租金很低且长时间未予调整的情况下(无论出于友情、帮助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该规则同样适用。[29]和前述美国法类似,这相当于给租金的提高设置了“涨停板”。[30]
5.租赁控制的宪法争议。与美国法一样,作为对所有权的直接干涉,德国租赁控制制度也受到了宪法诉讼的挑战。对此,德国宪法法院在多个判决中强调,住宅在人的生活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保护承租人的合理信赖不受出租人随意解约损害符合基本法第20条规定的“社会国”(sozialstaat)原则,是对所有权的必要限制。[31]在近年的有关判决中,德国宪法法院提出承租人的权利也是基本法第14条第1款项的财产权(eigentum)的一种,使解约限制更多了一层合宪的理由。[32]
二、住房租赁合同控制的社会经济效果
不仅在美国和德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对租赁合同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制度。[33]为什么租赁控制制度被广泛地采用?以下尝试从社会经济效果分析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部分以价格管制模型为基础,主要讨论理论界对(纽约市)租金管制的分析评价;第二部分则讨论以德国为代表的在租金市场化背景下进行租赁控制的社会经济效果。
(一)作为价格管制的租赁控制
1.租金管制的可行性。经济学者首先质疑租金管制本身的有效性。在这方面,张五常的分析很有代表性。[34]他认为即使在租金管制的情况下,房屋仍会和在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下一样得到有效配置,即得到房屋的顺序依“出价”[35]高低而定。理由是虽然租金价格机制不能自动发挥作用,但替代机制如排队、寻租等可以发挥和价格机制一样的作用。该观点的不当之处主要在于简单地将价格控制后物品的分配机制缩小为“排队”或“寻租”等方式。实际上,正如上文对纽约租金管制法律制度的梳理所显示的,只要分配程序周全(妥当的资格审查、有效的监管和充分的随机性),赋予承租人对多付租金的返还请求权,规定房东不得随意收回房屋,明确租赁合同双方维护和修理房屋的义务,限制转租牟利,通常就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住租金而不导致张五常所描述的无效率后果。有学者研究表明,在租金管制的实践中,房屋的分配并不是通过替代价格体系(pseudo-price system)进行,而一定程度上是在有资格的需求者中随机进行。这也就意味着租金管制所带来的福利能够为(至少是部分的)预期受益人所获得,而不是以其他方式被分配转移。因此租金管制是可行的。[36]
2.供给不足与无谓损失。也有经济学者认为租金管制会导致供求失衡。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一部分生产者剩余转化成了消费者剩余,但因为生产能力未能得到充分地释放,市场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市场规模被压缩,大量可以产生交换利益即社会福利的交易无法产生,因此会导致一部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dead weight loss)。[37]
从理论上看,在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的情况下,长期[38]限制租金水平会导致供给不足(出租房短缺)是非常确定的。不过这一后果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39]作为“不动产”,住房具有相对稳定性,国家很容易通过不动产税等形式增加所有权人空置房屋的成本,促使其将房屋投放到租赁市场。尤其要看到,居住是一种特殊的需求:人对住房并不像对衣服、首饰那样有近乎无限的需要,通常也不会像服装、首饰那样经常性地更换。因此,有多余住房的所有权人往往不会因为租金低就不再出租房屋,除非管制后的租金水平降低到小于房屋维护成本的地步。从目前的经验研究看,在有租金管制的地区,如果法律的控制规范足够周全,出租房屋供给急剧下降的情况通常不会发生。[40]实际上,在不存在管制、租金过高的情况下,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获得住房,国家需要以更大的成本来建设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这也是通过国家干涉补贴弱者,也会导致无谓损失。因此,如果规则设计妥当,租金管制不仅不会降低出租房屋的供给,也不会降低住房的供给。例如,法律可以对(特定城区的)新建房屋规定租金管制豁免,以鼓励有条件的消费群体通过购买或自建解决居住问题。[41]
3.租金管制与不当分配。更有力地批评租金管制的观点认为租金管制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当分配(misallocation)。那些能够负担高质量住房的承租人无法获得与其收入相当的居住条件,那些按照经济标准只能负担较小住房的承租人却获得了额外的补贴,即租金管制导致了违反经济规律的效果:未将住房分配给对其价值评价最高的人,从而造成(经济学意义上)不必要的“浪费”。对此,edward l. glaeser等进行了论证并通过实证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纽约市房屋不当配置的情形明显高于无租金管制的其他地区,租金管制严格的曼哈顿区的不当分配情形高于同城中的其他区。[42]
对于“不当配置”的存在,glaeser和luttmer首先通过构建一个线性模型证明供给不足并不是租赁控制的主要成本,他们发现,如果因租赁控制导致的房屋供给量的减少低于50%,则不当配置比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更高。[43]另外,在房屋异质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城市越久远,房屋异质化程度通常越高),对不同质房屋的租赁控制就可能破坏不同类型房屋之间的比较价格,因而不当分配的可能性更大。
接下来glaeser和luttmer通过计量模型对纽约市租赁控制所造成的不当配置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首先通过不同的标准对人群进行了分类,并假定不同人的居住面积是有差异的,且大致有规律可循,具体内容是:(1)高中毕业或肄业生的居住面积通常小于大学毕业或学历更高者;(2)无小孩家庭的居住面积通常小于有小孩家庭的居住面积;(3)年龄小于等于35岁的居住面积比年龄大于35岁小于等于60岁的居住面积小;(4)独居者的居住面积通常要小于三口之家的居住面积;(5)人均收入处于末三分之一的人的居住面积通常小于人均收入处于前三分之一的人。然后比较了纽约市和无租赁控制的其他美国城市中的住宅面积分配情况,发现除了第4组外,在其他各组中,纽约市房屋不当配置的情形明显高于无租赁控制的其他地区。[44]
两位作者同时还从其他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比的结果基本印证了“存在租赁控制的地区比无租赁控制的地区存在更显著的住房不当配置”这一结论。具体包括:(1)在纽约市内,租赁控制全面而严格的街区如曼哈顿(26.1%)比租赁控制宽松的街区如bronx的住房不当配置水平高(13%)。[45](2)在和与其具有一定相似性的芝加哥(人口规模相当,并且也有大规模供出租的公寓楼)、哈特福德(地理接近)的比较中,纽约市的住房不当分配水平(20.9%)要高于后两者(分别是7%和4.5%)。[46](3)通常不同期限的租赁所受到的租赁控制程度是不同的,作者所整理的数据表明,相对于短期租约,受到较强控制的长期租约带来的不当配置水平更高(相差近10%)。[47](4)以上的分析都是以房间数作为房屋的主要特征来分析有关房屋是否发生不当分配。作为检验,作者将该标准更改为卧室的数量或维修工作的数量[48],也同样发现纽约市房屋不当分配的状况仍然明显。[49]总结地说,该文的作者在这项迄今为止最全面、严谨的关于租金控制的实证分析中,成功质疑了认为租赁控制会导致房屋的质量或数量降低这一传统经济学观念,认为房屋的不当分配是租赁控制中更重要的福利损失的根源,并通过数个全面而精巧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验证。
不过,对该文的假设、分析与结论,仍需谨慎对待:其一,和大多数经济学者一样,作者只是假设收入或学历高的人应该被分配给价值较高的住房,而不考虑社会公平的因素,甚至也忽略了该项安排所可能导致的其他经济成本。其二,是否有效率在不动产市场中是很难验证的。一方面,即使在没有租金管制的市场中也存在着其他形式的各种管制,如所得税、规划、少数群体聚居、反歧视等,这些都是对自由市场假设的偏离,其广泛存在严重干扰对租金管制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的正确判断;另一方面,因为房屋的异质化高,房屋市场的信息一直处于高度不透明的状态,该文的研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应真实情况,仍有疑问。其三,该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时表明,租金管制所导致的不当分配的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比较而言,无论是否存在租金管制,其他地区同样存在不当配置的情况,纽约市的住房不当配置水平只比其他城市高出10%-15%.实际上,就像作者的对照研究所表明的,在纽约,那些本不受租金管制的独立所有房屋和住房数小于5的小型住宅楼中,也存在相当高的不当配置(分别是15.9%和11%)。这说明租金管制更多是发生转移分配的效果(将财产从出租人转移给承租人),而没有过分人为地刺激需求。可以这样解释:从租金管制受益的承租人有两个群体,因租金管制而得以在原本无法负担的住房和居住区生活的群体和因种种原因(如工作、家庭的需要)宁愿支付高额租金也要在特定地区居住的群体,租金管制降低了他们的租金负担,而后者占相当比例。
4.租金管制与劳动力市场效率。有人认为,控制租金会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劳动者为了保有低租金的住房而不愿意搬到较远的工作地点从事新的工作,从而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性;或者,即使到较远的地点从事工作,也会选择通勤而不是另租一套新住房的方式,导致通勤的成本增加。[50]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并不足以反驳租金管制。首先,如果一国每个地方都存在租金管制,并且能保证租金水平相对于住房质量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就不会明显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因为在其他地方同样可以找到合适的住房。而租金管制原本就应是在较大地域范围内考虑的事情,至少是应在一个可通勤的范围内通盘考虑的。其次,如果租金因为没有控制而过高或租赁条件因为缺乏控制而很差或不稳定,人们获得住房的方式就会转向购买。对于并不富有的人来说,购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而不能过多考虑与工作地点距离的因素,加上一旦购买,很难更换的现实,对劳动力流动或通勤成本影响可能更大。
5.住房租金管制的执行成本。租金管制的执行成本殊难测算,这是影响租金管制决策的重要变量。在范围上,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成本和司法成本。前者指管理机构的运行成本,后者指租赁合同当事人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争议而引起的费用支出。
6.租金管制与税收补贴。曾有学者建议通过税收的方式来间接实现租金管制,如对不动产的拥有者征收较高的不动产税,以补偿经济地位较弱的承租人。但税收的安排是一个普遍性的转分配制度,法律无法确保将房屋所有人的利益直接转分配到特定地区有特定需求的承租人身上。例如因为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与住房支出差异巨大,收入水平就不适合作为确定补贴数额的依据。另外,以税收形式转移支付也有成本,尤其是税收从征收到使用的各个过程都会存在不当的浪费,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无谓损失。其与租金管制相比很难说更优。
7.住房租金管制的社会收益。具体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保障基本人权。长久以来,住宅被认为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因而其分配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价值的权衡,还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量。这也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将其列为基本人权的原因(第13、25条)。不过,仅依此项就认为应进行租金管制并不妥当。首先,国家提供住宅保障的能力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若国家积累有限,自不应加之过重的义务(如为租金管制而支出行政成本)。[51]其次,虽然住宅权对一部分人(无住宅者)而言是重要的基本人权,但若通过租金管制的办法加以保护,会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出租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这也是基本人权,简单地厚此薄彼,很难谓妥当。这就是前文美国或德国都在宪法诉讼案件中进行周全考量的原因。因此,即使经过细致权衡后,这些国家的宪法裁判认为租金管制于理于法有据,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出于“保障基本人权(住宅权)”的考虑,而应视之为多项基本权利权衡取舍之后的结果。
(2)避免贫富聚居。城市中收入较少的居民通常无力购置私有住房。在没有租金管制的情况下,因为无法负担“高尚”住宅区的昂贵租金,这类居民只能选择向租金较低的社区搬迁,从而逐步形成社区的分化。传统上决定租金价格的因素很多,当出现优良住宅区和贫民窟的对立时,这种对立本身也将成为影响租金价格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住宅分区化越严重,分区本身对房屋价格的影响越大。若不及时干涉,一旦分区(gentrification)的结构形成,将只会恶性循环,导致进一步的区域分化。[52]实际上,即使从纯经济学的视角看,住宅分区也不完全是市场有效运行的结果。设有两个相邻的社区a和b,都没有租赁控制,但是社区a的租金高,b的租金相对较低,无租赁控制的后果是将社区a中的穷人和贫民驱赶到社区b,使后者的居住条件恶化,社会问题丛生。这本质上是社区a将一部分本应负担的社会成本外部化给了社区b,无偿占用了社区b的资源。[53]当然,正如“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是人的自然需求,因此住宅分区是城市发展中自始就有的现象,若不形成明显的贫富对立等社会问题,法律并无干涉的必要。[54]
(3)增进社会和谐。学者margret j. radin很有说服力地指出,租金管制可以使承租人相对长久地居住在一个住宅中,因而有助于加强邻里的关系,增进社区的和谐,增强对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度。若无租金管制,人们会被迫为寻找便宜的居所而频繁迁移,不但容易导致邻里关系异化,使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拖后,也容易使人丧失归属感,降低对社会的信心。[55]当前,尽管社区、邻里关系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降低,[56]但还不至于彻底消失,因此租金管制的此项社会收益仍能成立。
总之,在目前关于租金管制成本的分析中,能够成立的主要是两项:不当分配所产生的不恰当激励;租金管制的执行成本。相对应的,租金管制的社会收益有三项:在不过分损害所有权的前提下保障人“居住”这一基本需求(人权);避免贫富聚居;促进社区稳定与和谐。这里,社会收益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租人的数量。对租赁人口比例超过60%[57]的纽约市而言,实行较严的租金管制很难谓不当。十余年前,经济学者richard arnott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与法辞典》[58]撰写了“租金管制”(rent control)这一辞条。他指出,实际上租金管制本身也在变化,从“第一代”僵硬地控制租金,禁止出租人以任何形式解除租赁合同,到“第二代”允许租金随市场适当上调,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解除租赁合同,甚至允许出租人在与新承租人签订合同时自由确定租金。[59]比较而言,“第二代”租金管制并不直接,其对租赁市场的负面影响也更不容易观察。权衡各派观点后,arnott最终只好这样做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对现代租金管制制度影响的判断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
(二)以降低租赁合同成本为目标的租赁控制
当前的德国租赁法也可以说是“第二代”租金管制的代表。如前所述,目前德国住房租赁合同制度已基本转为市场导向——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以自由约定租金,该租金可根据市场行情逐年上调。与(中国)租赁合同自由制度不同的是德国法限制了出租人的解除权,强行排除了出租人单方决定租金上涨数额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率的安排。
在关于合同成本的理论中,oliver e. williamson曾指出,缔约中的交易成本受以下三因素的影响:交易的频繁度(frequency)、交易的形式与不确定程度、交易中资产专用性程度(asset specificity)。其中,资产专用性所引发的交易成本最为显著。[60]正是这一因素的存在,在长期合同关系中,协商地位较弱的一方常会受另一方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因为前者常会在合同之外进行一些以合同稳定或可履行为前提的其他投资,若另一方可随时解除合同,这些投资便将失去保护。[61]尽管在缔约前,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一旦合同达成,该方当事人为履约进行了必要准备后(如买方为配合即将交付的特种机器设计了专用的模具),便对资产的使用失去了选择权——此时对方当事人客观上对该资产享有“垄断性”的合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专用财产的所有者便不得不依赖合同相对人,对相对方的毁约和事后盘剥缺乏防范手段——只要给他造成的损失小于其寻找新合同相对方的成本,就会忍受相对方的背信行为。
套用这一分析框架,住房租赁合同的交易成本很高,因为:(1)居住是对稳定性要求较高的需求,因此住房租赁合同的缔约频率较低,交易各方基本不具有重复缔约的机会,无法形成程式化的缔约协商机制;(2)住房租赁合同是长期合同,而合同持续时间越长,不确定性越大;(3)在住房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有大量的“交易专用性资产”,包括装修、家具、邻里关系以及在工作、生活上所作的其他投资。[62]理论上,在没有特殊的外部规制时,承租人仍有两个途径保护自己的专用性资产投入。其一,事先约定较长的租赁期限;其二,在出租人无故解除租赁合同时要求其赔偿信赖利益等损失。不过,现实中这两种方式都缺乏可行性:(1)缺乏周全的租金调整条款,出租人通常会不愿意接受长期租约,而租金调整条款事先往往很难确定,如出租、承租双方往往很难就具体的租金上涨的比例达成一致;(2)承租人以住宅为中心的很多投入在性质上都是非资产性投入,很难计算和证明其价值。在法律没有特别保护承租人的倾向时,法官通常也不会支持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而做出的“信赖性”的投资。[63]
退一步讲,即使考虑到如果承租人拒绝续约,出租人不得不重新装修房屋,张贴广告寻找新的承租人,因房屋空闲而减少租金收入,从而解除也会给出租人带来相当大的损失这一因素,承租人与出租人也形成一定程度的双边垄断的关系,双方都会有机会主义或策略性行为的动力,其围绕续约而发生的讨价还价的成本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互相要挟以至于两败俱伤)。[64]总之,对住房租赁合同而言,若无规制而仅凭市场或自我调节,很容易发生逆向选择的后果,即,若出租人的解约权没有限制,将使承租人不敢以租赁住宅为中心做过多的投入,从而反过来使承租人更倾向于选择短期性的租赁安排,进而导致出租人无法对承租人履行长期租约形成充分的信任,如此恶性循环,双方的福利都会受损害。
正如oliver e. williamson所指出的,在交易专用性财产价值很大而无法自我调节时(如企业将上下游产业整合在一起),便有必要通过适当的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加以辅助。[65]德国法上的租赁控制制度——强行要求当事人签订长期租约,禁止以解除合同为手段谋求租金上涨——便可以解释为是这样一种规制结构。
德国法上的解约限制除了有保护专用性资产的效果外,还有稳定租赁关系的效果。在无法律规制的情况下,若经济增长幅度大,出租人会不惜以解约为代价谋求上调租金,从而使住房关系过分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起伏不定,造成缔约、解约频繁,社会平均租期缩短等后果。一定程度的解约限制则可以使租赁合同免受或少受经济的波动影响,同时又不违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最终节约缔约与解约成本,因而长期来看是有效率的。统计显示,德国租金水平增长幅度相当稳定,并未过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可资证明。[66]
有恒产,方有恒心。对于土地这种注定无法人人拥有的稀缺资源,人们通过物权法创设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当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制度,把一些原本的合同权利提升为物权,以保障稳定预期,鼓励长远的经营与投入。法律限制住房租赁合同的解除,也是同样的道理。[67]
三、中国住房租赁控制的制度建构
(一)历史与现状
1.近代史上的租赁控制。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便出现了城市住宅短缺、租金高涨、出租房质量低下等问题。[68]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开始出台法律文件对租赁关系予以规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解决房荒为目的的房屋救济立法时期(1929-1936年)、以战争为背景的全面租金管制时期(1937-1943年)以及战后租金管制立法的修正与补充时期(1945-1949年)。[69]
1949年以后,在延续了民国法统的我国台湾,不再有真正意义的上的租赁控制制度。其“土地法”第97条虽然对房租数额有所限制[70],但作用有限。[71]“土地法”第100条虽然仿照德国体制对住房租赁合同的解除设置了限制,但因该条仅适用于不定期租约,而法律上又没有限制定期租约签订的配套规则,因此很难真正发挥作用。[72]不过法律技术上与租赁控制相似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50余年来一直发挥着效力。[73]大陆在建国后后,虽然废除了旧法统,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旧有的租赁控制规则,直至1956年前后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如多个城市都规定:“可供居住的空闲房屋或超过需要之房屋,遇必要时,得由人民政府限期命所有人或管理出租或出借。”[74]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后,逐步确立了城市公房出租制度。这是一种最极端的租赁控制——国家(多数情况下以企事业单位为媒介)垄断全部的住房供给,全面控制租金水平和租赁合同的内容。1980年,中国启动了公有住房改革,基本思路是“出售公房,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75]1992年,将房地产业确立为支柱产业,重点扶持发展。[76]鉴于有大批城市居民既无法“建房买房”,也无法享受租赁公房的福利,面临住房困难,近年来国家开始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77]
2.住房租赁制度现状。在当下中国,住房租赁有制度包括公房租赁、廉租房和私房租赁几种形式。根据2007年的统计,北京、上海户籍人口中通过租赁公房解决居住需求的分别占总人口的15%和20%.[78]公有住房的租金水平一般比较低。根据2000年的一项统计,公有住房租金水平占双职工家庭平均工资的比重为6%-10%左右。[79]现行廉租房制度的问题主要是覆盖面极小,只针对符合特定条件(双困户)的城市户籍家庭。[80]2008年底,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央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解决近750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240万户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并积极推进农村危房改造。[81]但其执行状况仍待观察,另外,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其覆盖面仍然有限。
在私房租赁方面,1990年代以后,建设部和一些省市分别制定了题为“城镇(城市)房屋租赁条例(管理办法)”的地方法规或规章。[82]有些地方的工商局和国土房管局制定了《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83]供签约者参考。这些法律或范本基本上对住房租赁持自由的态度,如规定:房屋租金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租赁期限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合同;禁止未经所有人同意的转租,否则合同无效等。当前对私有住房租赁合同不多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治安、税收管理上。如规定租赁合同应备案,[84]个人出租住房所得按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85]等。实践中,对于治安和税收登记,无论出租人还是承租人都没有充分的动力,因此两项制度都很难执行。
总体来看,公房租赁主要用于解决事业单位的遗留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慢慢退出市场,廉租房制度则主要着眼于城市低收入家庭,二者适用范围都是比较有限的。相比而言,随着房屋自有率的提高,随着购买第二套、第三套住房人数的增加,私房租赁市场必将日益扩大。虽然城市私房租赁市场也分为多种层次,如城乡结合带的租赁、城中村的租赁与一般城市房屋的租赁等,但只是用途不同而已,需求本身并无差异,因此可一并讨论。
(二)住房租赁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对于未来是否应实行一定形式的住房租赁合同控制,宜着眼于不同的租赁控制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1.租金管制模式。首先,如前所述,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租金管制是否必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保护承租人的数量。只有在承租人的数量足够大时,对所有权施加限制才有充分的正当性。[86]在这里,“多数”还是“少数”不再仅仅是量上的差别,而是质的不同。如前所述,从实证数据上看,在实行较强租赁控制的德国、美国纽约、新泽西州等,承租人都占超过50%的比例。这为其租赁控制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相比而言,在中国,因受看重田土房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目前城市居民房屋自有产权的比例是比较高的。[87]因此,在规模较大的城市,私有住房租赁的比例并不是很高。[88]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的租赁控制(租金管制)难言正当。
其次,必须要看到,住房问题的解决除租金管制以外还有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方式。相比而言,租金管制的长处是在现有住房的基础上解决居住成本的问题。在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城市中居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有限的住宅总量无法满足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新增人口的居住需求,以北京为例,在当前1633万的城市人口中,有近420万[89]的流动人口[90],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因此在商品住宅建设之外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也很必要,租金管制至多能限制租金,并不能提升住宅总量。
从可行性看,租金管制的有效运作,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条件:第一,有较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司法裁判系统。在目前中国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低效、不透明、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如果实行租金管制制度,行政成本和寻租成本将非常高,若安排不当,很容易产生一个官僚化的强权部门,为规避者提供寻租的温床,甚至可能违反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第二,单一产权住宅楼的比例较大。所谓单一产权的住宅楼,指整栋住宅楼都归一人所有,其将楼中的住宅分别出租给不同的承租人。在进行租金管制时,所有权人虽然可以用将有关房屋出卖的方式规避,但法律可以通过对单一产权住宅楼转为区分所有住宅楼进行限制来加以阻止,而限制区分所有的住宅或独栋住宅的转让是非常困难的。[91]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单一产权住宅楼的情况下,如果再普遍性地管制转让价格,更将危及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有效运行。第三,有全面的不动产税制度。通常认为不动产税有助于抑制房地产投机和过大的住房需求(税收压力可促使人们选择适当的房屋大小和房屋类型),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92]就租赁控制而言,不动产税可以防止房屋闲置,因而是租金管制制度的重要前提。在中国尚未开征不动产税的背景下,即使规定租金管制,部分所有权人也可以选择将房屋空置而使该制度无法实现其目标。
2.解除权限制模式。德国法上的租赁控制是以市场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前述租金管制模式中的两项成本都不显著。其主要收益是降低租赁关系中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避免出租人通过策略化行为获益,维护租赁关系的稳定。这对中国目前住房租赁制度的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中国住房租赁市场中,租赁期限通常都比较短,多数人对租赁合同缺乏稳定预期。[93]
若能修正合同法第232、236条,借鉴德国法的相关制度,限制出租人解除权,引入市场标准作为租金调整的基准,将非常有助于增进中国住房租赁交易的效率。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安排:(1)借鉴德国法上限制定期租约的制度,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签订有期限的住房租赁合同;(2)改变合同法第232条的规定,将不定期租约视为长期租约,除非具有正当理由,不得解除;(3)改变合同法第234条对转租的严格禁止,允许承租人在短期外出时将房屋未经允许临时转租他人(但不得转租牟利);(4)具体建立指导租金体系,为租金上涨提供依据。[94]
在借鉴他国的制度时,还应注意中国各地差异较大的特点。即并不应完全排除未来在某些城市实行纽约模式的租金管制的可能性,尤其在某一地区承租人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半数或半数以上比例时,实行较为严格的租金管制,并无不妥。
(三)住房租赁控制制度要点
总体而言,一套行之有效的住房租赁控制制度需要满足五项要求:(1)租金可负担。如前所述,租金管制的程度是两种不同租赁控制模式的最主要差异。在住房紧缺,城市又无从扩张的情况下,适当限制租金水平是必然选择,限制的具体值可以参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确定,如将租金额控制在每户家庭总收入的30%左右。这一安排除了可确保租金可负担外,也可以“过滤”富有的承租人,让真正需要租赁控制保护的人获得相应的福利。当然,任何控制都应有充分的正当化理由,承租人占多数,住宅租赁市场紧张(如前文纽约市将租金管制与租赁房屋空置率挂钩)是管制租金的必要条件。若欠缺此二者,则应考虑借鉴德国的做法,将管制着眼于合同的解除,而由市场确定租金。(2)房屋适居。纽约州上诉法院法院将租赁视为“栖居处所与服务”的买卖(sale of shelter and service[95]),“所有权人应确保有关房屋适合人类居住,符合当事人关于租屋质量的合理预期,无任何危及承租人生命、健康和安全之处”,可资借鉴。(3)租期稳定。这要求有效限制定期租约的签订,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4)出租人有合理回报。任何形式的租赁控制,都必须确保租金高于房屋的维护成本,否则必然导致所有人放弃所有权。为此,在制定租金标准时,要专门测算房屋的维护成本。(5)防止承租人滥用法律保护。这需要制定必要的资格审查、限制转租牟利和其他规避行为等规则。
四、结语
住房是一项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为对私人之间住房交易进行规制提供了合理性和可能性。第一,住房是必需品。作为“衣食住行”中的一项,住房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住宅不仅是一项商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基本人权——尤其是(中国政府长期强调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第二,住房是其他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俗语强调“安居乐业”即是此理。这意味着其关乎社会的安定。第三,住房(土地)是近乎永久存续的耐用品,这意味着对其进行规制是可能的。[96]
就租赁合同社会控制的具体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市场化”的控制,不直接限制租金数额,主要着眼于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同时为出租人提供市场化的租金参照标准;另一种则以租金管制为中心,配套以解除权限制、强制维修、防规避等规则。在价值判断层面,即使是相对极端的纽约式的租赁控制也有其合理性,不能轻易加以否定。具体到中国,当前阶段,参酌德国的做法适当进行一些“市场化”的住房租赁合同控制,将有助于提高租赁合同的效率,是必要且可行的。未来若一些城市中的承租人比例急剧上升,适当进行租金管制亦是可选之项。
长期以来,笔者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这一命题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权利不得滥用”的观念上。即所有权应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一致,个人行使所有权应当顾及社会利益。对租赁控制的研究改变了笔者的认识。以上分析表明,所有权的社会限制绝不仅仅是权利不得滥用的问题,而是可以剥夺所有权的某些权能,甚至导致所有权的丧失(如导致房屋所有人抛弃房屋)。在人类社会中,土地与房屋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财产形式,对其的限制可以到这个地步,的确是令人惊讶的。在此,重温耶林的论断会有更深的理解:“世上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没有那种不需要考虑社会利益的所有权,这一观念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97]
【注释】
本报告的写作,得益于曾燕斐、贺剑、曹志勋、关重、茅少伟、李德妮的协助,得益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学术讨论组”(workshop)中邓峰、洪燕蓉、李启成、李清池、凌斌、陈端洪、薛军等同事、师长,尤其是访问教授陈子平、张伟仁的批评与指点,得益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研究员katherine wilhelm的帮助,得益于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胡涛教授的讨论,特此致谢。本文的缩减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25-139页。
[1] 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7-213页。milton friedman and george j. stigler, “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 in rent control: a popular paradox: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nt control, vancouve: the fraser institute, 1975, pp. 87-102; bruno s. frey, et al., “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 1984, p. 986 ff.; richard m. alston, et al., “is there a 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in the 1990'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1992, pp. 203-209. 1984年一项题为“经济学家的一致与不同”的经验研究发现,对于“租金管制会影响房屋供给的质量和数量”这一命题,75%的美国和德国经济学家同意,而只有45%的奥地利经济学家,20%的法国经济学家同意。frey, et al., consensus and dissension among economists: an empirical inquiry, 74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6 (1984); 1992年一项以美国经济学家为对象的统计调查印证了这项研究,有大约76%的人一般性地同意这一命题。alston, et al., “is there a consensus among economists in the 1990's?”, 82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3 (1992)。
[2] 参见edgar o. olsen, “is rent control good social policy?” chicago-kent law review, vol. 67, 1991, pp. 931-932.
[3] 参见housing maintenance code (title 27, chapter 2 n.y.c. admin. code)。
[4]官方的统计,见timothy l. colli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york city rent guidelines board and the rent stabilization system, 2006, p. 278, 2006年9月15日,http://www.housingnyc.com/html/about/intro/toc.html,2009年2月20日。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并不统一,有人认为租赁控制导致了房屋质量下降,如raymond jackson, “rent control and the supply of housing services: the brookline massachusetts exper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52, no. 4, 1993, pp. 467-475;也有人认为如果监管与鼓励措施得当,未必发生房屋质量下降的效果,如choon-geol moon, et al., “the effect of rent control on housing quality chang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1993, pp. 1135-1144.
[5] 参见block v. hirsh, 256 u.s. 135, 156 (1921)。 另请参见marcus brown holding company, inc., v. feldman, et al., 256 u.s. 170 (1921)。 在该案中,针对纽约市租赁控制的宪法诉讼也被驳回。new york's proposed rent control act, yale law journal, vol. 50, 1940, p. 178.
[6] 参见chastleton corp. v. sinclair, 264 u.s. 543 (1924)。
[7] 参见clarence eisen v. oliver c. eastman, 421 f.2d 560, 567 (1969)。
[8] 参见joseph william singer,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05, 2nd edition, p. 476.
[9] 若空置率小于5%,则意味着租赁的供求关系仍处于紧急状态,租金管制应继续维持;若空置率大于5%,则意味着供求不再紧张,租金管制应予解除。9 nycrr § 2100.19. 根据统计,从1960年到2005年,纽约市出租房屋的空置率一直在1.2%至3.2%之间徘徊。timothy l. colli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york city rgb and the rent stabilization system, appendix y.
[10] n.y.c. admin. code section 26-501.
[11] 如2003年纽约市租赁法(rent law 2003)将租金管制延长至2011年6月15日,届时将重新表决。
[12] 如pennell v. city of san jose, 485 u.s. 1 (1988); lingle v. chevro, 544 u.s. 528 (2005)。 另见胡建淼等:《美国管理型征收中公共利益标准的最新发展》,《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
[13] 参见n.j. stat. § 2a: 18-61.1; n.j. stat. § 2a:18-61.1. f…… 除新泽西州外,哥伦比亚特区、新南威尔士、康涅狄格等州也有类似规定。参见robert s. schoshinski, american law of landlord and tenant, rochester: lawyers cooperative pub. co, 1980, § 1: 1, p. 5.
[14] n.j. stat. § 2a: 18-61.1.
[15] robert s. schoshinski, american law of landlord and tenant, 1980, § 1: 1, p. 5.
[16] n.j. stat. § 2a:18-61.1. f.
[17] 见《德国民法典》第566条(原第571条),注意该条仅限于住房,不适用于商业租赁。
[18]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ii/1, c. h. beck, 1986, 13. aufl., s. 255.
[19] reichsmietengesetz v. 24.3.1922; mieterschutzgesetz v. 1.6.1923; wohnungsmangelgesetz v. 26.7.1923; wohnungsgesetz v. 8.3.1946; staudinger╟emmerich (2006), vorbemerkungen zu § 535 bgb rn. 1-13.
[20] 比较大的改革包括1960年6月23日通过的《住房强制经济削减法案》(bgbl i 389),1963年7月29日通过的《租赁合同改革法》,1971年《住房租赁合同解除限制第一法案》(wrkschg v. 25.11.1971),1974年12月18日通过的《住房租赁合同解除限制第二法案》(相关资料见德国联邦议会的立法理由汇编:bt-drucks. 7/2629),1994年的住房租赁法改革(相关资料见的立法理由汇编:bt-drucks. 13/159),最近的一项租赁合同制度的重大改革是2001年6月19日通过的《租赁合同改革法》(相关资料见的立法理由汇编:bt-drucks. 14/4553)。
[21] 目前,德国法上对租金的直接管制仅限于“社会保障住房”(sozialwohnungen),分别规定在1974和1994年的两部法律中(bgbl i 137; bgbl i 2166)。另请详见德国1994年进行住房租赁法改革时jürgen sonnenschein出具的专家意见。jürgen sonnenschein, mietrecht: wohnraummiete ╟ eine analyse des geltenden rechts, bt-drucksache 13-159, s. 389.
[22] 1954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bettermann曾撰文指出,“承租人保护法的核心是持续性保护,即确保租赁关系的长期性,尤其是其中的解除权限制规则。”bettermann, mieterschutz und vertragsfreiheit, jz 1954, 461 (461)。
[23] 该规则主要用来鼓励企业或个人为雇员建造宿舍。即若届满后将其租给雇员使用,签订定期租赁合同是允许的。bt-drucks. 15/4553, s. 70.
[24] 例如,在将房屋交给亲属使用时,需在告知中说明亲属的姓名和相关个人信息。ag düsseldorf zmr 2006, 160; ag berlin-mitte mm 2005, 147; annegret harz, et al., handbuch des fachanwalts miet- und wohnungseigentumsrecht, newwied: luchterhand, 2006, s. 501.
[25] 德国宪法法院在一个判决中指出,如果出租人有两套住房,则无论另外一套是否正被出租,出租人原则上都不得以此为理由解除租赁合同。bverfg njw 1993, 1637.
[26] bghst 30, 280, 281 = njw 1982, 896.
[27] 但法律对此只提供了两种提高租金的约定形式:一是双方对未来不同时段(该时段须至少为一年)的租金作出明确约定(§ 557a bgb);二是将租金的数额与联邦统计局所发布的生活价格指数(preisindex für die lebenshaltung)相挂钩,可据此逐年调整(§ 557b bgb)。
[28] 对于可比租金的确定,法律规定了三种方式(§§ 558-558e bgb)。一是地区租金指数(mietspiegel),该指数主要反映过去两年内本地区的租金水平。通常由出租人协会与承租人协会共同或由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测算。二是准租金指数(qualifizierter mietspiegel),指在没有建立租金指数制度的地区通过抽查、专家意见等方式形成的对租金水平的分析。三是租金数据库(mietdatenbank),指通过对一段时间内的租金统计形成的数据库。
[29] 参见staudinger-emmerich (2003), § 558 rn. 46 bgb.
[30] 参见bt-drucks. 9/2079, s. 16; bt-drucks. 14/4553, s. 36, 53 f.
[31] 参见bverfge 37, 132; 68, 361.
[32] 参见bverfge 89, 1, 5 ff.; bverfg nzm 2000, 539; martin ibler, die eigentumsdogmatik und die inhalts- und schrankenbestimmungen i.s.v. art. 14 abs. 1 s. 2 gg im mietrecht, acp 197 (1997), 565 (574 ff.)。
[33] 参见richard arnott, “rent control: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1, 1988, pp. 203-215; stephen malpezzi, et al., “rent contro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129, 1991.
[34] 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第187-213页。
[35] 指名义价格与各种规避成本(排队、行贿、支付黑市高价等)之和。
[36] edward l.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2003, pp. 1030-1031.
[37] 相关介绍与文献参见edward l.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pp. 1027, 1030.
[38] 住房是耐用品,弹性较差,因此短期内的租金管制并不会导致供给下降。即,紧急状态(如战争)下的租赁控制只会发生转分配的效果,而不会导致无效率。关于住宅耐用品属性意义与作用的论述,还可参见edward l. glaeser, et al., “urban decline and durable hous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2005, p. 345. 作者指出,鉴于住宅的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即可完成,同时住宅又具有耐用性(因而拆除或改建很难),因此在人口涌入城市时,城市会急剧膨胀,而衰落则是个缓慢的过程。
[39] 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目前证明租金管制导致供给不足的经验研究很少。目前能检索到的只有pollakowski以美国麻省坎布里奇市为对象所进行的研究,认为租赁控制导致了近20%的供给减少,不过其模型的设计还有讨论的余地。henry o. pollakowski, “rent control and housing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deregulation in cambridge in massachusett”, civic report, no. 36, 2003, https://www.nmhc.org/content/servefile.cfm?fileid=3677, 2008年8月16日。
[40] 据统计,在1994到2002年间,纽约市的的租赁控制房屋总量减少了5%,但主要不是因为出租人拒绝将房屋出租,而是因为租赁控制的解除(见前述解除租赁控制的条件,如租金超过一定的限额:9 nycrr §§ 2201.2-3.)。见前引timothy l. colli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york city rgb and the rent stabilization system, appendix z.
[41] 在过去几十年内纽约市的新建住宅并未减少,而是每年都略有增加。见rgb《住房供给情况报告》,第17页(附录3),http://www.housingnyc.com/downloads/research/pdf_reports/08hsr.pdf,2008年8月13日。
[42] 参见edward l.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pp. 1037-1039.
[43]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p. 1031.
[44] 在第1至第5组中,纽约市房屋不当配置率比其他地区分别高15.4%,2.9%,6.4%,0和10.6%.当然,作者的分析只是指出了相对的差异,例如,在无租赁控制的地区,教育程度低的人居住面积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31.6%),之所以认为纽约市的租赁控制造成了房屋的不当分配,是因为纽约市相比而言,该数字更高(47.0%)。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pp. 1037-1039.
[45]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p. 1040 (table 4)。
[46]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p. 1043-1044.
[47]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table 6.
[48] 维修工作的数量间接反映了房屋的质量:通常房屋质量越好,维修的数量越低。
[49] glaeser et al., “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 p. 1041 (table 5)。
[50] 参见charles w. baird, rent control: the perennial folly, san francisco: cato institute, 1980, pp. 21, 40, 86; kaushik basu, et al., “the economics of tenancy rent control,”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2000, p. 959.
[51]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很值得重视:“我们并不蔑视舒适、安全、卫生住宅的重要性,但联邦宪法并不就每一项社会或经济上的病症提供司法上的救济。”lindsey v. normet, 405 u.s. 56, 73 (1972)。
[52] 参见note, “reassessing rent control: its economic impact in a gentrifying housing market,”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1, 1988, pp. 1835-1839.
[53] joseph william singer,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 p. 630.
[54] 关于城市分区以及住宅小区限制性条款(如限制房屋装修、用途、宠物饲养等)的研究,见福格尔森:《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朱歌姝译,上海:上海出版社,2007年。
[55] 参见margaret j. radin, “residential rent control,”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5, 1986, pp. 368-378.
[56] 参见黎熙元等:《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57] 根据rgb《住房供给情况报告》(2008),租赁住房占纽约市住房总数的67%(全美国的平均值为33%),见该报告第3页,http://www.housingnyc.com/downloads/research/pdf_reports/08hsr.pdf,2008年8月13日。
[58] peter newman, ed.,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the law,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59] 纽约市的租金管制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型,这在1970年代以后更为明显。richard arnott, “time for revisionism on rent contro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1995, pp. 99-120
[60] 参见oliver e. williamson,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2, 1979, p. 233 ff.
[61] 汉斯曼也有类似的论述。参见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36页。
[62]与住房租赁合同类似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也是一例。在最初进入劳务市场时,人可能有很多选择,很多雇主争相雇佣,但当其最终选定了雇主并为其工作几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的劳动技能可能已经专门化了,很难在重新适应新的工作,他已经在有关社区做了相当大的个人投资(从配偶的工作选择、子女上学到对社区服务设施的熟悉乃至社区人际关系等),也就是说,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从职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雇员越来越难以离开他当前的雇主。见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第36页。
[63] 实践中,即便是对装修这种很容易估值的投入,法官在面对赔偿请求权时也往往持很谨慎的态度,通常按装修残值来进行补偿,并要求承租人提供充分的证明(如第三方的评估意见)。可以想见,其他信赖支出的赔偿请求更难于得到支持。
[64]参见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第287页。
[65] oliver e. williamson,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pp. 244-245. 有关例示,参见该文第251-254页。
[66] 见德国联邦政府2006年的《住房补贴与租赁报告》(wohngeld- und mietenbericht 2006)(drucks. 16/5853),第15页。
[67]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德国有学者将住房租赁合同看作是房屋上的“物权性负担”(dingliche lasten)。staudinger-emmerich (2003), 578 rn. 7; vorbem. zu § 535 rn. 24 ff. bgb.
[68] 参见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1840-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5页以下。
[69] 参见张群:《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考略——从住宅权的角度》,《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
[70] 该条规定:“城市房屋之租金,以不超过土地及其建筑物申报总价额年息百分之十为限。约定房屋租金超过前项规定者,改管市县政府得依前项所定标准强制减定之。”
[71] 因为事实上房屋租赁制租金多远低于房屋实际价值之百分之十。参见谢哲胜书,第9页。
[72] 见“司法院”三十六年院解字第3489号解释。
[73] 见该法第2条(规定了地租管制):“耕地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约定地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不得增加。”、第17条规定了(租赁关系解除的限制):“耕地租约期满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二、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据者。”
[74] 如《上海市房屋租赁暂行条例(第六次草案)》(1949),第3条;《天津市私人房屋租赁暂行条例》(1951)第10条等。转引自张群:《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考略——从住宅权的角度》,《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
[75] 如《国务院关于印发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1988]1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鼓励职工购买公有旧住房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88]13号);《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1991年6月7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
[76] 参见《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发[1992]61号)。
[77] 相关规则,如2005年的《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5]405号)和2007年11月八部委局及人民银行发布的《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78] 参见《北京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上海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374页。
[79] 参见《国家计委、建设部、财政部印发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公有住房租金改革的意见的通知》(计价格[2000]954号)。
[80] 根据一项统计,到2006年底,全国享受租赁保障的家庭共有54.7万户,相比全国的庞大承租人群体而言,微乎其微。钱瑛瑛:《上海住房租赁群体租赁保障思路》,《上海房地》2007年第8期。
[81]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31号)。
[82] 除《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外,大多数省会和重要城市都有类似规定,如《西安市城市房屋租赁条例》(1997)、、《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1999)、《哈尔滨市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2005)、《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2007)等。
[83] 如2004年发布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还有《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示范文本(2006版)》。
[84] 如《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2007)第2章(第7-11条)。
[85] 参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86] 谢哲胜先生亦有同样见解:“房租管制法律通过与否之决定性因素在于承租人人口之多寡”。谢哲胜:《房租管制法律与政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90页。
[87] 根据200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国72%的城市居民拥有所住房屋的产权。其中,大城市的自有产权比例较低,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和珠海),产权私有比例是54%.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7年,北京、上海这两大城市中户籍居民自有住宅比例上升到80%.见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统计年鉴》(2007),2008年,第185页;《西安统计年鉴》(2006),2007年,第176页;《上海统计年鉴》(2007),2008年,第374页;广州市统计局:《广州统计年鉴》(2007),2008年,第240页;《山东统计年鉴》(2007),2008年,第232页;《浙江统计年鉴》(2008),第186页;《河南统计年鉴》(2008),第255页。
[88] 以2007与2008年为例,各省市户籍人口中租赁私房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不足1%,西安1.14%,上海1.6%,广州2.4%;山东、浙江、河南均低于1%.数据出处同上注。这些数据虽然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做出的统计,但即使把流动人口考虑进来(去除农民工、大学生等住集体宿舍的人群),私房租赁的比例也仍不超过30%,因为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都不超过30%.
[89] 参见朱富言等:《北京市流动人口数量变动趋势分析》,《西北人口》2008年第4期。
[90] 流动人口指没有城市户籍但是在城市居住超过半年的人口,笔者这里假定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没有房屋所有权,而且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口是农民工,居住在条件很差的临时住宅中。
[91] 美国各州的具体限制方式仍有所差别。其中,纽约市的限制最为严格。如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有超过35%以上的承租人愿意购买分拆出售的房屋,出租人才能将有关楼房出卖,否则承租人可以继续租用原住房。关于该制度的具体说明,参见david a. fine, “the condominium conversion problem: causes and solutions,” duke law journal, vol. 1980, no. 2, pp. 320 ff.
[92]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物业税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张再金:《物业税改革的经济影响:一个文献综述》,《税务与经济》2008年第1期;黄茂荣:《不动产税及其对不动产产业的经济指导》,《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93] 在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主持的一项调查中,天津市住房租赁合同的租期通常为1年,占所调查租赁合同总数(354份)的95.8%.见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天津市住房租赁抽样调查情况分析报告》,《华北金融》2006年第2期。在福州,63.8%的租赁住房合同租期为12个月,27.6%的合同租期为6个月。见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课题组:《2007年度福州市住房贷款及租赁市场抽样调查分析》,《福建金融》2008年第4期。房屋中介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现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的调查,在问及被调查人“买房前是否考虑过租房”时,81.09%的借款人表示不曾考虑租房。在问及“考虑过租租房,但仍然选择买房的原因”时,57.69%的借款人认为租房没有归属感。很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一些城市如北京的租赁市场上,过渡性的一居室供不应求(供需比为1:2.4),而本可用于家庭长久居住的三居室却供大于求(供需比为1.3:1)。数据来源:北京市建委城建研究中心报告。
[94] 在这个问题上,完善现行房地产管理法中地价确定、价格评估和价格申报等制度即可(第32-34条)。
[95] park west management corp. v. arthur mitchell, et al., 47 n.y. 2d 316, 325 (1979)。
[96] fridrich a. hayek, the repercussions of rent restrictions, in rent control: a popular paradox: evidence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nt control, p. 68. 该文是哈耶克1930年在k?nigsberg的演讲辞,原文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社会政治协会会刊》(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上。注意这里只强调可能性,是否正当或必要是另外的问题,上文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97] rudolph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4. aufl., 1878, s. 7. 后世的英美法学者如bruce ackerman和joseph w. singer也认为,所有权人应当为承租人提供宜居的环境并索取适当而不是过高的租金,本质上是源于所有权社会责任的义务,是对相关主体在所有权上的信赖利益(reliance interest)的保护。bruce ackerman, “regulation slum housing markets on behalf of the poor: of housing codes, housing subsidies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policy,” yale law journal, vol. 80, 1971, p. 1171; joseph w. singer, “the reliance interest in property,”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0, 1988, pp. 659-663.(北京大学法学院·许德风)